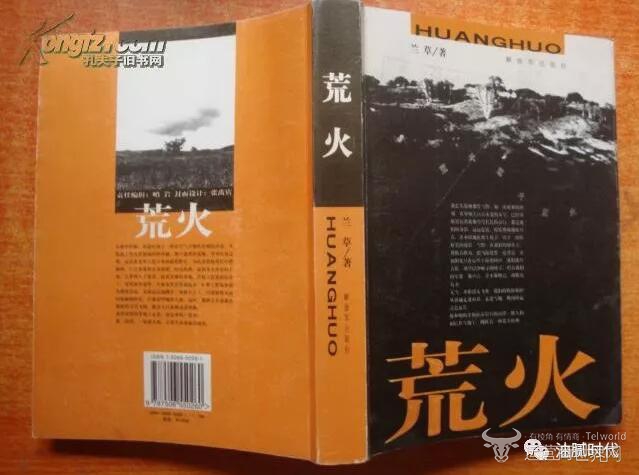奔跑的华哥 /文
专栏作者简介:奔跑的华哥,知名企业战略管理专家、自由作家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,从业电信业十年、航空业八年,现任央企子公司高管。个人公众号ID:奔跑的解忧杂货铺。

1
知文、陆者众,知张、王者寡。
1233年蒙军灭金后,次年起在西起陕川、东至淮河下游的数千里战线上同时对南宋发动进攻,宋蒙战争全面爆发。到1279年,这场鏖战持续近半个世纪。
东线战事以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张世杰“三杰”抗元为人所众知。1279年2月,崖山海战失败,君臣与十万军民蹈海。
激烈的西线战事则少有人谈及,它最终以1279年四川军区司令员(制置史)兼重庆市委书记(知府)张珏被俘殉国、合州地委书记(知州)王立保民献城而告终。
从全局看,人们所公认的是,重庆、合川防线的顽强抵抗,牵制了蒙元大量兵力,防止了敌人利用长江水道东下江南,否则南宋王朝绝对坚持不到1279年崖山战役。
张、王二公,一死一降。死者,与文公一样,是不得不死;降者,则已成千古公案了。
宋朝的末世公务员难当啊,降或不降,死或不死,都由不得自己,都有大讲究。
2
体贴的重庆朋友最知道俺。忙里偷闲半日,一定要安排去看看湖广会馆。于是,冒着五月的毛毛细雨,我们在午后来到了东水门长江边。
中国历史上有八次大移民运动,这里有“江西填湖广,湖广填四川”之说。这个在原来大杂院基础上重修的古建筑群倚山临江,拾阶而上好几进,做工精细而修旧如旧。更值得赞赏的是对明末清初的那次移民有详细的记述,收集了不少民间遗物。三百年多年前,祖先们自江南一带而来,风尘仆仆于巴渝崎岖的道路上,那是怎样一种情形呢。
晚上与另一位朋友会面,到嘉陵江畔趸船上的酒楼去吃江鲜,点了几种鱼,名字之古怪,刚才还犹在唇边,现在全然记不得了!然后开车在两江之上穿梭,换不同的角度欣赏雨夜壮观又柔美的山城。
回到南方君临酒店,已是午夜时分。好奢侈的“巴山夜雨”,还竟然有青蛙和虫子的鸣叫声撞击我高达21楼的窗棂,是我的幻听吗?
游完重庆,次日要去合川。我是第一次听说那里有个在蒙古铁骑下死守了36年的宋军孤城遗址,名叫钓鱼城。如此巨大的悬念,颇感震撼心魄。

3
要说这当年镇守于重庆、合川抗元防线的张、王,得先说说我的老乡贤余玠。
余玠之死,是南宋在西线陷入困境的开始。
脱脱的《宋史》有《余玠传》,说他是湖北蕲州人。实际上,老脱有所不知,余公实际上是江西修水人。从修水县城往南30公里眉毛山下,有黄沙镇汤桥村,1197年小余出生于此,后随父母过长江,迁居湖北蕲州。
小余毕业于江西白鹿洞书院。他潜心兵学和朱熹哲学《太极图说解》,颇有心得。1234年,进入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府,江淮抗蒙八年,屡建奇功。1241年,他官至任淮东军区副司令(制置副使),成为淮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者。
1242年六月,余玠出任四川宣谕、制置使兼重庆知府。当时全川州郡大部分已沦陷于蒙军铁蹄。余玠临危受命,行前向皇帝发誓:“愿假十年,手挈全蜀之地,还之朝廷”。
余玠赴川后,调查研究,制定了治蜀纲要《经理四蜀图》,轻徭薄赋、革除弊政,整顿军纪、广纳贤良。其中,有两条很关键:
一是发动地方势力,动员流散力量回川,建立了耕战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体系,实行人民战争,又保经济生产。
二是建立山城防御体系,据险筑城,以步制骑。他沿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和长江两岸山隘要道,筑青居、大获、钓鱼、云顶等十余城, 堡垒里储备粮食,形成以钓鱼-重庆-泸州-嘉定(乐山)为核心的防线。当蒙军进攻,就将军民撤到堡里坚守,保全地方政权;当蒙军攻势缓和,则出动骚扰对方,耗其粮草,迫其退兵。
1246年,蒙军分兵四道入蜀以来,余玠凭山险制骑,激战凡36役。1250年,余玠调四川各路精锐北伐,三战连捷。1252年,余玠率军击退进攻乐山(嘉定)的蒙军。理宗下旨称赞他“著八年经营之功,敌不近边,岁则大稔”,聘他为兵部尚书,仍驻四川。
而中国历史之吊诡之处,在此又要显露无遗了!

4
老余大刀阔斧,得罪了一个小人,云顶堡垒一个叫姚世安的统领。姚正好结识当朝川籍左丞相谢方叔的一个侄子,通过贿赂,谢方叔利用职权开始发出针对老余的各种诬告。
宋朝皇帝对武将有一种深刻的恐惧感。当初太祖以“陈桥兵变”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。这成了有宋赵家皇帝们的“原罪”。
具体到宋理宗赵昀,则更有阴暗一面。他只是宁宗的远房堂侄,被权臣史弥远看中,被立为沂王。宁宗一死,史弥远联合杨皇后假传遗诏,废太子赵竑为济王,立沂王为帝,是为宋理宗。
也就是说,这个理宗压根儿没想到自己能当上皇帝,内心一直惶惶不安。史弥远一死,他内心的不安全感更甚。
这些因素,让宋理宗做出糊涂透顶的决定。他发出金牌,召余玠进京。
这个御前金牌,当时最快也要16天。如果理宗有手机就简单了,给老余发个短信:亲,有事找你,回来喝酒。
据说老余接到短信前,也给理宗发了个短信:亲,身子骨不爽,昨晚与将士庆功,可能多喝了两杯。
接到我短信就装病是吧?理宗不信,奸臣们不愿信,继续催余玠进京。接到余玠重病消息的第十天,理宗又做出更糟糕的决定:免去余玠职务,让余晦接替。
这个余晦可不是老余什么亲戚,而是一个平庸的临安府尹。当余玠得知朝廷决定后,忧愤之中病情加重,1253年7月竟病逝于任所,时年48岁。
1937年秋,修水《八贤祠志》修成时,李烈钧撰序,冯玉祥、林森、于右任、居正、邵力子、戴传贤、李宗仁、叶楚伧分别为八贤题像赞。在《八贤祠志》民国26年手抄油印本中,于右任题写了“余义夫公像赞:十年西蜀,治臻上理。宋室屏藩,惟公是倚。仪型百世,精神不死。”
写到这,我操起手机给九江的丁伯刚兄发了条信息,问:“汤桥在宋代有个叫余介的名将?”
片刻,这个汤桥跑出来的大作家回了信息,顺便帮我改了个错别字:“对,宋代的,余玠”。

余玠像
4
余公死后,几任继任者依靠其八年经营的基础,苦苦支撑,而期间,蒙军在占领区开展屯田与练兵,稳扎稳打,四川形势已越来越坏。
1258年秋,蒙哥率军4万分三道入蜀,迫近合州,遣宋降将至钓鱼城招降,为宋合州守将王坚所杀。持续到1279年的著名宋元鏖战“钓鱼城之战”,由此展开。
1259年2月,蒙哥亲征合州,7月,被王坚军炮击中,不久死于军中,年仅52岁。蒙哥死后,他在叙利亚、湖南一带作战的弟弟们纷纷回师争夺汗位,使欧洲战场和蒙宋战争都得到了缓解。
而此时,中国历史中的幽灵又该登场了。
1260年,权相贾似道忌王坚战功,使帝诏其回京城临安。1264年3月,郁愤已久的王坚病逝。而同一年,忽必烈继任汗位,重起战事,很快攻陷重镇泸州,危及宋军核心防线。
此后,蒙军在“汉奸”们的帮助下,改变战术,开始在川大举屯田、筑寨、训练水军,稳扎稳打,逐步扭转被动局面。1271年,蒙在成都设四川行省,1273年破襄阳(大家知道,郭靖郭大侠和蓉儿夫妇在此殉国啊哈哈)。1278年春,元朝集大军围困重庆。

张珏像
5
有人说余玠死得比岳飞还要冤,而张珏的死,就又落俗套了。在宋代,当朋友的重要责任之一,可能就是要操心朋友的名节。与文天祥一样,张珏也是被朋友“劝死”的。
我有时奇怪,那些劝人死的,自己为何却能在异族的羽翼下苟活呢?
重庆-合州防线,以合州钓鱼城为要塞,是余玠的堡垒防线核心组成部分。从1243年到1279年宋朝灭亡,在此大小200余战,期间,王坚、张珏、王立先后任知州,与重庆互为犄角,成为合州抗击蒙元的军政领袖。而重庆却先合州沦陷于敌手。原因很简单,乃是因为重庆守军内部将领投敌。
襄樊失守后,入川道路已被阻断,重庆为中心的西线已成孤地。1275年五月,张珏接任四川制置副使、重庆知府。
张珏,陕西凤县人。18岁从军合州知州王坚部下,守合州钓鱼城。他足智多谋,英勇善战,被誉为“四川虓将”。
危难之中张珏就任后,立即被陷入各种诱降的口水当中。先是泸州降将李从来诱降,遭张公严词拒绝。随即,成都总兵李德辉又递来劝降书。
他写的一段话,则值得玩味,曰:“君之为臣,不亲于宋之子孙;合之为州,不大于宋之天下。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,汝犹偃然负阻穷山,而日忠于所事,不亦惑乎?”但张珏仍不为所动。
张珏不降,但终于败于内部叛将之手。1278年2月,诱降不成的蒙军,对重庆发动总攻。部将赵安打开重庆镇西门。张珏督师巷战,寡不敌众,要饮毒酒自尽,但被左右阻止,他只好率余部、携妻子乘舟东下涪州。《宋史张珏传》说,他“中道大憾”,半路上后悔,觉得要死在重庆,于是要沉船一死,却被部下夺其斧,欲跳水自尽,却被部下拖其衣。几死不得,终于在涪州被蒙军俘虏。
张珏被押在西安赵老庵囚所。1280年的某日,他的老友前来探望,对他说:“公尽忠一世,以报所事,今至此,纵得不死,亦何以哉?”您为宋室尽忠一世,以报国家,今日走到这一步,纵然能不死,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?
张珏闻言深以为然。待老友走后,趁元兵看守不备,张珏解下弓弦,自缢殉国,终年67岁。文天祥闻讯,在北京狱中集杜诗写《悼珏诗》,发出了“向使国不亡,功业竟何如?”的浩叹。

6
在5月的温润的风里,同行的有重庆的朋友们。脚下芳草萋萋,我们则谈笑风生。
重庆失守,犄角顿失,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。镇守钓鱼城合州知州、原张珏的部将王立,则面临另一种机会与挑战。
钓鱼城位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,山并不高,但嘉、渠、涪三水汇流,有山水之险,也有交通之便。站在城头,大好江山尽收眼底,可谓风景无限。
遗址颇有规模,保存完整。城门城墙、武道衙门、步军营、水军码头等遗址,有钓鱼台、护国寺、悬佛寺、千佛石窟等名胜古迹,还有元以来大量诗赋碑刻,做各种各样的历史咏叹。
而此时的王立,也始终处于诱降的阴谋当中。
攻陷重庆后,元军一鼓作气,大举进攻当年成为蒙哥折戟的钓鱼城。王立自1276年底起率领军民守城,奋战两年多,最终弹尽粮绝。这两年,合川大旱,粮草缺乏,易子相食。川内全境基本已落入元蒙之手,钓鱼城早已成为孤城。
有趣的是,这时又戏剧性地冒出一个漂亮的女人,是元朝安西王王相李德辉同母异父之妹、元将领熊耳的夫人。泸州战役中,她被宋军所俘带回钓鱼城,为王立所得,对外称义妹。她隐姓埋名,谎称姓王,暗中联络李德辉,以保住合川十几万军民劝说王立投降。王立为其所动,1279年4月,在得到世祖忽必烈“不屠城”的承诺下,王立出降。至此,西线战事结束。
据记载,弃城后,守城的32名(一说36名)将官全部拔剑自刎。而忽必烈念王立功劳,封节度使,仍然兼任合州知州。
又据记载,王立后来又做出复宋的举动,事败,1301年被赐死,年仅50岁。
7
王立的献降所引起的争议,自元代以来延续至今。
元初学者刘熏(土旁)作有《补史十忠传》,追怀宋末死节之士。在赞扬张珏的同时,对王立颇不满意,其子刘麟瑞更是大为感叹:“吾君不负吾宁死,遗恨谁怜快敌仇!”
在钓鱼城历代忠义祠中,王立、熊耳夫人、李德辉的牌位被反复移进移出,反映了人们巨大争议。
1942年6月,郭沫若先生的《钓鱼城访古》中又重提了这“遗恨”二字。他的诗云:“卅载孤撑天一线,千秋共仰宋三卿。贰臣妖妇同祠宇,遗恨分明未可平!” 贰臣者,王立也。妖妇,就是熊耳夫人了。
我们几个老朋友,也在钓鱼城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记得我的观点是:不论哪个时代,一个政府官员,不以民生为己任,而以个人“名节”为标准,这种思维让人不寒而栗。若他象明末的范浩民一样,先救下百万将士的性命而受缚,最终自尽以示效忠朝廷,当然可以以“国士”称之了。
事实上,王立后来被元政府继续任命为合州知州,谁又说这不是合州百姓的幸事呢?
8
值得一提的是,这小小的钓鱼城里,倒有不少唐代以来的文物留存至今,包括唐代的身长达11米的悬空卧佛、千佛石窟、护国寺等。不过,这些经历了当年长达30多年战火的宝贵文物,却没能逃得过当代的政治运动的摧残,而留下了累累伤痕。
当年张珏所树的“王坚纪功碑”的命运,就更有意思了。先是元朝认为纪念抵抗他们的王坚是有问题的,因此把碑石雕刻成千手观音。但这座千手观音却最终毁在“文革”造反派手中。其毁坏情状,惊心动魄,惨不忍睹。这称之为“遗恨”,大约是没有错的。
更可寻味的是,在历史潮流面前,我们常说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,但大势又是如何形成的呢?都是量变到质变。忠贤之士难以申其志,真正的遗恨就怕难免了。